憂鬱的熱帶藝術
- chin lee gan
- Dec 17, 2025
- 13 min read
如果世界上藝術精華,沒有客觀價值標準來保護,恐怕十之八九均會被後人在權勢易主之時,或趣味改向之時,毀損無餘。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梁思成, 1944
1
如今,對於馬國這個移民社會里的華人來説,所謂家,屬於一個怎樣的具體存在?精神上的家園,又傾向何處?有人説,一部世界藝術史,等同於人類的精神史,依此邏輯,若要知道馬國華人心繫何處,與其相信不怎麼老實的主流媒體所樂於宣傳的熱帶笑容,倒不如相信藝術家眼裏的憂鬱氣質。
兩週前,我出席了獨立導演譚偉富與胡美庭的《回家、離家、搬家》短片放映會。放映會上,播映了《我和阿古斯妲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天涼好個秋》、《弄邊》,和《孝》一共四部短片,所有短片的故事都圍繞在回家、離家、搬家這樣的內容概念展開。其中,《弄邊》給了我較深的悸動。在這部屬於半自傳式紀實短片裏,導演藉着一次回弄邊老家(Rompin)探親的過程,將人聲喧譁的富都車站、令人沉沉欲睡的長途巴士、患上話癆症的印裔德士司機、堅實矗立着的新村木屋、對愛情充滿嚮往的大學女友、永遠都在煩心的媽媽、需要按時吃藥的爸爸、愛喝酒但其實顧家的哥哥、羞澀於表露感情的自己,以及那條沿路伴着油棕樹的南北大道,一律線性串聯起來,並讓情感緩緩地流淌,非常含蓄,也非常真實。這是許多漂泊在外的新村孩子對於老家的情感啊!
《弄邊》這部短片以紀實手法拍攝,片中人物皆非專業演員,各自以自己熟悉的方言表達,印度話與蹩腳的馬來話也適時穿插其中,雖然整體看起來生澀,但卻生動得恰如其分。作為觀眾,我深深感動於導演還原現實的藝術堅持。放映會的末段交流時刻,一名資深觀眾提問:“為何不全程用華語作為語言媒介?”這名資深觀眾自稱看過台灣電影兩百部,並推崇台灣金馬獎為華人電影世界第一獎,所以獻議導演該將目標瞄準金馬獎,由此,將來所拍攝電影也該以華語表達為主。
先不論衡量一部電影優秀的準繩,該不該建立在評委能否明白電影裏的言語上,或爭論拍電影該以表達或得獎為主,我彼時腦裏首先浮現的想法是:為何馬國華人總是那麼‘若為現實故,一切皆可拋?’
2
《弄邊》的鄉愁,倒使我想起了《金城小子》這部由台灣導演侯孝賢與姚宏易聯袂以影像記錄畫家劉小東回鄉畫畫的紀錄片。
《金城小子》獲得了第4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然後,片裏的人都説東北話。
金城是中國畫家劉小東的東北遼寧的老家。離家30年到北京發展繪畫事業,據劉小東説,這次選擇回鄉創作,是想趕在小鎮被徹底城市化以前,記錄點滴存在過的一些人事物。後來在台北誠品書局展出的《金城小子》個人畫展裏,一共展出了劉小東回鄉時創作的大小三十餘張油畫及紙上作品。這批創作,記錄了他這年來回家的情感軌跡,和兒時成長記憶。
有個詩人問過劉小東:四處飄泊的人根在哪裏?他回答:出生地。作為現實主義畫家,劉小東的創作向來關注生活周邊人物的生存狀態,和他們對精神家園的依戀。早在《金城小子》裏的城鄉矛盾以前,他的《三峽大移民》系列作品也刻畫了因三峽水壩工程而被迫搬遷的重慶、湖北兩省的百萬移民。這是他最早在畫作裏表現建設與犧牲的二元矛盾。
他在回老家畫畫以前,曾跟友人喝酒時感慨道:“我們的記憶都餵狗了,沒有東西可以證明我們曾活過。我們的記憶被膨脹的發展吞食了。”
3
話鋒至此,大概‘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這類使人腦力暈眩的問題大概便要上場了。
歐洲自航海時代掀幕開始,便頻繁上演商人/海盜到處掠奪資源的戲碼,同時,各國殖民者有了大量在異域佔據殖民地的機會。對於另一些哲人來説,他們則積極在化外之境尋找烏托邦,藉由未被文字侵襲的荒蠻部落,淨化文明帶來的疲憊。例如高更(Paul Gauguin)這名畫家,他在法國仍是歐洲文化中心之際,卻質疑自己存在的意義起來,經過一番折騰,最後終於拋棄了優渥的證卷行職業,在大溪地找到讓他大放光芒的藝術能量,也遇見了他那生命中的毛利族情人。
不過,在歐洲東邊的亞洲大陸裏,由於野心家的侵略,國勢動盪,大舉遷徙南洋的中國人顯然沒有這種在異域裏折磨自己精神,並尋找自我的奢侈。這些華人南來的目的,做生意有之,被賣豬仔更多,皆旨在避開戰亂,尋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早期在馬來亞刻苦求存的華人命運,便是在這樣的框架下匍匐前進。馬來亞經歷過數次被殖民的經驗,後在各族先賢合力爭取國家獨立後,才開始了現代化的過程,自此,大多數華人也才決心落地生根,履行社會契約,效忠馬來西亞政府。
馬國藝術家黃海昌在《她在14歲就嫁人,現在有14個孩子》裏,以自己的家庭結構為框架,刻畫了他祖母這名南洋移民的精神面貌。與許多華人的祖母一樣,這位形象堅毅,兒女成羣的畫中主角,為了生計而必須不辭勞苦地穿梭於橡膠園林之間。但她的臉上同時布滿無力感,彷彿憂心着十四名孩子的生計之時,仍得面對同化的問題,還有那無止境的遷徙命運。1
一圖訴萬語,黃海昌的這張作品,烙印着早期華人家庭的刻苦精神與生存狀態,成為了移民社會最生動的寫照。
雖然如此,華人遷徙的命運,至今依然持續進行着。跟據馬來亞大學的鄭乃平教授所指,自新經濟政策執行以來,超過一百萬名華裔馬來西亞人出走,移居海外,其中多為專業人士。2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更光明的前程,更公平的施政,許多華人陸續出走,做為施政不公的無聲抗議,以致在後殖民時代的馬國社會里,華人祖輩的移民身份一直被他族一再提醒,並時刻嘲諷其欠缺歸屬感的過客性格。
‘住得不滿意就回你老家去’!
無法不令人熟悉的措辭。無關知識水平,出口挑釁的人還包括校長。
可是,回哪裏去?
4
於是,約定俗成似的,我們一般隨時強調自己是華裔馬來西亞人,或馬來西亞華人。“馬來西亞才是我們的國家”,回應馬來至上主義之餘,順道強調給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知道:“嘿,別再喊錯了!”也許是多元敏感社會帶來的身份焦慮症。華裔馬來西亞人在馬國獨立後,一般都調整了自己和‘祖國’的位置,而效忠於第二故鄉——馬來西亞。自此以後,中國人就是中國人,漢族、藏族還是塔吉克族,都不太列入華裔馬來西亞人關心的範圍裏了,取而代之的是,華人在新祖國裏的新朋友,以及各種身份與權益問題。文化對焦,也由此開始投射在椰林蕉風之間。
保皇派和改革派的鬥爭,則成了隸屬祖輩的情感記憶,如今對於出生地在馬國的新一代華人來説,可能興致缺缺,即便知道了,也只‘得個知字’,無關痛癢。
不過,如今在面向大中華文化圈的語境裏,華人可以這麼分成兩派:親中派和民主派。3親中派無他,基因裏的商業嗅覺使其虎視眈眈於中國廣大市場,因而視中華文化為一座發亮的拱橋,才極力推崇母語教育;民主派則長期對應於馬來民族主義,在思想上不同意於強權與宗教治國, 積極爭取參與建國所該獲得的公民權益,並相信於多元復調模式,才是促進族羣和諧發展的治國態度,為此才發力維護母語政策。
雖然兩方都認同於維護母語教育這一環,但目的不同,教出來的氣質,豈無分別?而學習這檔事一旦功利起來,視野就要變得狹窄了。馬國教育圈流行的讀書為考試、考試為文憑、文憑為高幣值的學習氣氛,你我皆心照不宣。所謂華人文化,在國家獨立以後,恐怕只剩母語教育一環受到高度注重。這始於受到強權無理壓制的高度反彈。可惜的是,母語當前卻只被許多新一代華人視為一種便於簡略溝通的工具,再無深層要求。這也掐斷了華人文化學術研究的源頭。
鄭良樹曾經在《大馬華社與中華文化》一文裏,敍述了馬國華人文化傾斜發展的現象,他認為,飲食、休閒、娛樂此類世俗生活文化在華人圈裏大行其道,漢學研究及中華文化則乏人問津,欠缺大量願意深耕的人才。4黃文斌對此做出補充,除了政府行政偏差,這也與華社偏重工商社會的‘功利觀念’有關。他還説,若與馬來文藝界相比,馬來友族對民族自身文化創造的自覺與努力,不容忽視。5
此外,安煥然也在《馬華文化依然是表演文化》文中重申,馬國華社今日雖然仍孜孜於舞獅舞龍、二十四節令鼓、古廟遊神等文化活動,即使這些文化品牌在‘大中華文化圈’算稍有名氣,但當中精神卻已從早年的憂患吶喊,過渡成了純粹展演的狂歡。他問道:究竟馬華本土能否培養出學術大師,而非僅僅鬥士?6
只是,人們不自覺捨棄文化包袱的速度,恐怕比鬥士爭取文化自尊來得快。
5
因吉隆坡捷運而強硬徵收蘇丹街的計劃,再次敲響了華人文化歷史面對發展洪流而被迫消失的警鐘。
上個世紀中旬,中國政府為了現代化進程,大力推動城市改造計劃,其中一項被學者稱為文化災難的計劃,便是罔顧知識界的阻擾,魯莽拆遷數千條北京老城區和老胡同,破壞了北京城原本卓越宏偉的佈局與構圖。有位清華建築系教授因此感嘆道:“我們正在毀滅這座偉大的古城,不是因為戰爭、革命,而是因為建設”。
因建設之名,如今馬國捷運公司一樣魯莽地罔顧百年曆史建築,打算讓捷運路段穿進蘇丹街這條百年老街,並聯同土地與礦務局祭出土地法令,威迫蘇丹街業主簽署徵地協議,並以蠻橫姿態嗆聲:‘發展必有犧牲’。惟發展若要割捨國家文化遺產的話,這筆糊塗賬,再次反射了馬國政府一邊嚷着走向文明先進國之時,卻一邊讓文化歷史記憶走向萎靡的無知態度。蘇丹街是吉隆坡老社區異常重要的一條街,活古蹟——人鏡慈善白話劇社、樂安酒店、鄺福榮洋服、百代影社等許多仍然活生生矗立在該街上,它們作為吉隆坡歷史與文化碩果,不僅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生活理想,也肩負着美學價值的傳承任務。
不過,在這次蘇丹街徵地風波里,需要反思的是,華人對待自身文化傳統與歷史的自覺,仍舊不及馬來友族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熱情,及具體落實於生活裏的文化實踐。仔細想想,在蘇丹街被捷運公司打起如意算盤、覬覦捷運周圍地段日後升值帶來的回饋以前,是不是先被華人自身慢慢淡忘了其文化價值,及歷史意義?
譬如上面所提到的《弄邊》短片放映會上的觀眾獻議,在華人羣體裏,恐怕依然充斥‘過於務實’的心態,恰如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形容的那樣,華人是務實者與現實主義者。因此,所謂歷史與文化牌匾,在現實面前,都能擱置於角落,贏了局面再説。再如安煥然所形容的,馬國華社經常只把文化傳統,擺在表演和娛樂這種輕得過份的位置上,使其淪為提高民族尊嚴的過場角色。
在乎的,永遠僅僅在於一堆數字遊戲——每年不斷爭加的學校新生人數,持續保持上揚的總體學校成績,銀行户口裏陸續增加的個人財富,添置一間又一間的洋房地產——用以象徵成功、進步。
那文化建設呢?
6
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在華人圈子裏,有些人在有感自身文化遭受冷淡待遇之時,為了驅走寒意,才勉強從儲物間取出了關於五千年文明的舊牌匾,讓彼此在優越感下互相取暖。然而代價便是,走向文化對話的腳步,因此躊躇不前。
不過種族藩籬架得更高的原因,也許來自1969年的種族衝突。
影像工作者梁友瑄在台灣藝術大學學習多年,對照單一民族的城市結構以後,同樣糾結於家國種族政策帶來的身份迷思,隱隱覺得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時刻提醒自身民族的命運。為了瞭解撲朔迷離般的69年種族衝突,及瞭解513事件為其母親帶來的心理陰影,梁友瑄拍攝了《傷城》這部記錄短片,在片中藉由跟母親的幾次對談裏,摸索母親記憶裏的傷痕碎片,讓母親在情感焦慮中慢慢得到緩解。梁導演在記錄片中後段,重遊了故鄉檳島的一些歷史古蹟,並嘗試敞開腳步,走入過往曾因怯意而始終抱持陌生的友族文化活動裏,希望藉此消除心裏疙瘩,拉近距離。
互聯網崛起以前,308以前,這樣的歷史課題,永遠無法被廣泛討論,怯弱的媒體,失衡的報導,每每自有解釋的套路,所謂平衡報導,卻縱容了更多跋扈姿態,讓霸權下的弱者只能在咖啡店宣泄。 面對碎片般的歷史記憶,和斷垣殘破的文化習俗,所謂完整的國民人格,猶如缺了支撐胸膛重心的腰椎一樣,無法直挺;也或許憧憧歷史陰影一直尾隨,乃至不願放下身段,馬國華人只好持續出走,到更文明的國度,在更自由的空氣裏大口呼吸,才能理直氣壯論證自己的存在價值,找到存在感。
法國人類學家,也是結構主義代表的列維·斯特勞斯卻選擇了從文明走向原始,反思文明進程。他在二戰前寫過一本在異域裏尋找自我的著作,叫《憂鬱的熱帶》,試圖在各個原始部落的習俗、神話、語言、圖騰裏思索社會架構,釐清現代化的種種權力關係,對社會學領域帶來諸多貢獻。裏頭,他寫過這麼一句話:“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交流越少,它們就越不可能為對方所腐蝕;但另一方面,在這種情形下,這兩種文化各自的使者也就越不可能掌握他們之間差異的豐富性和重要性”。7
惟在馬國,面對差異性截然相對的友族文化,這個豐富性,恐怕仍然停留於飲食文化交融的水平裏。
不,如今還多少摻和了斯里蘭卡和孟加拉的味覺記憶。
7
捷運徵地事件以前,蘇丹街、茨廠街等這些老社區因為全球化、城市科技化等原因,老居民逐漸外遷,舊式營業店屋和文娛活動還沒來得及轉型,便已消退在年輕華人的視線以外,加上僱傭外勞熱潮,促使大量各國外勞進駐區內,對準外勞需要的各種商業店鋪如外幣兑換店、外勞中介所、餐館、旅社等紛紛林立,因此,對許多新一代的華人來説,吸引力漸弱,寧願卻步於外。雖然該地毗鄰富都車站,來來往往的遊客與乘客,仍然絡繹不絕,但是昔日實在的老街區情懷,就要急速褪色成黑白,僅能通過講古活動,才能喚醒人們的歷史記憶。
蘇丹街老街坊杜志昌醫生在捍衞百年老街的講古活動上,根據其阿爺著作《杜南先生哀思錄》及成長記憶,娓娓道出蘇丹街上曾經存在過的偉大人、事、物。對照那些許多影響過華社先賢的精神,再看當今老社區的凋零景象,以及被強制徵收的命運,讓人陡然倍覺荒涼,心生酸楚。百年老街依然矗立着,人猶如此,拆遷以後,人何以堪?守護文化,便是守護精神生活,面對歷史,文化,言語,建築這些重要文化載體,華人若然持續抱持隨看隨拋的務實心態,集體精神走向頹靡,指日可待。
在這場蘇丹街徵地風波中,扮演要角的建築學者張集強明確指出了保存老街道的重要性。他説:“這些老街道,以及街道上的建築、老商號、店屋、老居民等,是構成吉隆坡歷史的最主要元素。因此,要保存吉隆坡的歷史,應該要朝向保存完整老社區的方向來思考。在這樣的條件下,蘇丹街即使不是最老的一條街,它仍然是構成老吉隆坡最主要的一條街。倘若蘇丹街失守,當局計劃中的商業大樓完工,將牽動整個地區的產業經濟,老吉隆坡社區的容貌必將消失殆盡。如果都市發展只重視經濟價值而忽略了人文價值,最終只會形成一個沒有生命(soulless)的都市”。8
由此,張集強強調:“事情演變至今,球已不在業主或捷運腳下,而是端看民眾對這件事情的回應。權力機構的優勢是,沉默即代表認同,如果民眾對蘇丹街的徵收事件沒有強烈的主張,即代表整體社會的多數站在捷運公司那一邊。因此,如果你還關心蘇丹街的未來,關心吉隆坡的歷史及文化遺產,就沒有理由到這時候還不出來舉手表態”。9
對於熱衷危言聳聽、渲染情緒的藝術工作者來説,我必須在此補上一槍,作為本文總結——這何止關心百年老街的命運而已,捍衞蘇丹街,長遠來看,等於預防民族文化精神從精神憂鬱走向精神衰弱,這比各家關心自家孩子在學校裏考多少個A,還重要得多啊!
8
行為藝術家劉德梁想得周到,知道馬國華人處尊養優,慣於沉默,耽於憂鬱,所以選擇犧牲肉身,穿透大街小巷,積極提醒民眾的人權意識及公民權益,讓願意表態的各種階層人士在其肉體蓋上‘蘇丹街Jalan Sultan’的印章,象徵支持這場捍衞運動。
惟肉體只是浮雲,聚散有時,存活在世上短暫得可憐。況且只在肉體表皮上蓋個章,表形卻難以表意。在蓋章的同時,有否也把先輩歷史與理想也刻在心底,這個難度,值得深思。
注一:資料引自[馬]Karim Raslan《東南亞行旅漫記》,林青青、康中慧譯,星洲日報出版社,2004年6月,第211頁
注二: 資料參考[馬]潘永強< “回去”中國:出去或嗆聲? >一文,見《我們的時代精神》,吉隆坡,燧人氏事業,2011年11月,第47頁
注三:這個比喻引自[馬]黃進發<大中華民族主義有利華社嗎?>一文,見《獨立新聞在線》,2010年11月14日
注四:<大馬華社與中華文化>,鄭良樹,《社會變遷與文化詮釋》,何國忠編,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出版,2006年
注五:<從錢穆持守傳統文化的意義反思馬華文化之建設>,黃文斌,《社會變遷與文化詮釋》,何國忠編,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出版,2006年
注六: [馬]安煥然<馬華文化依然是表演文化>,見《星洲日報》,2012年1月14日
注七:<作為英雄的人類學家> ,[美]桑格塔《反對闡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4月第2版,第79頁
注八: [馬]張集強<蘇丹街的保存意義>,見《星洲日報》,2011年10月16日
注九: [馬]張集強<獨立遺產大樓VS百年遺產老店>,見《星洲日報》,2011年12月25日
(本文刊登於《獨立新聞在線》獨立藝文,31/01/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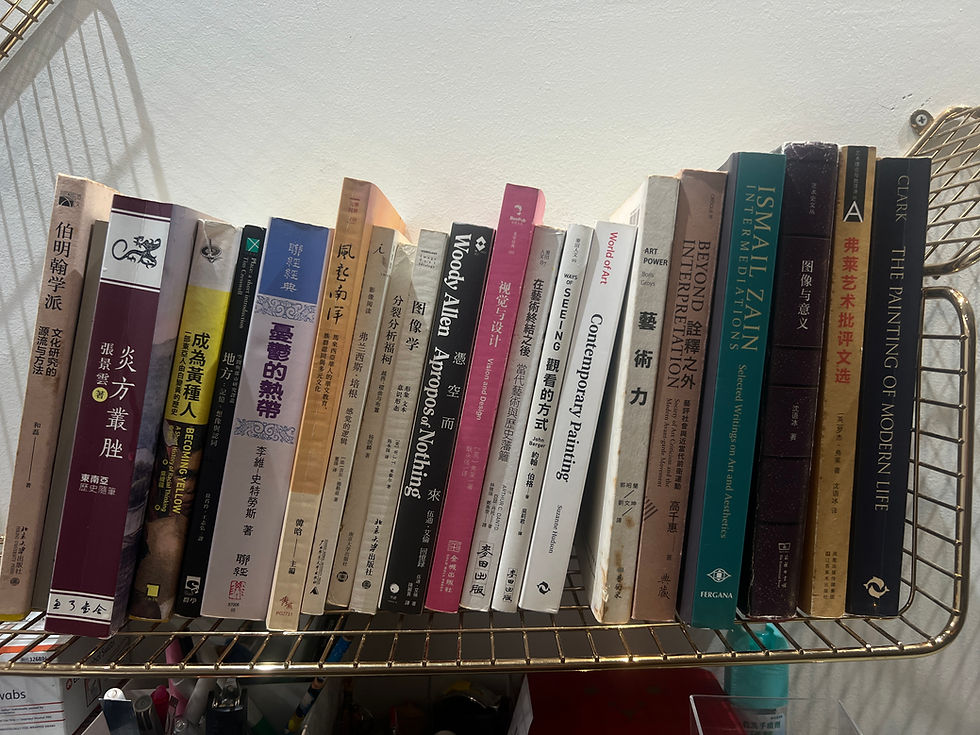

Comments